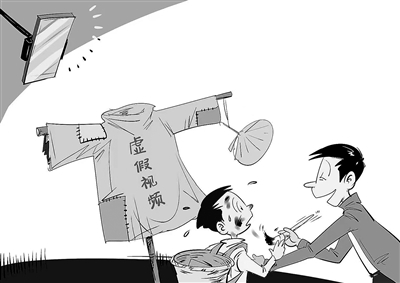新年第一個交易日,創業板上市公司華策影視股價跌停并創上市新低,公司市值一天縮水16億元。之后的兩個交易日華策影視持續低迷,1月4日,在市場大幅上攻的情況下股價也僅僅微漲0.51%,3個交易日市值蒸發20億元。
剛剛過去的2019年元旦假期,文藝圈最熱門的話題,不是在維也納和柏林舉行的兩場古典音樂的傳統盛宴,也不是網友對各大衛視車禍現場般跨年演唱會的吐槽,而是朋友圈當中圍繞電影《地球最后的夜晚》的一場罵戰。
這部電影之所以能引起如此高的關注度,是因為它憑借一個傲人的紀錄,改寫了中國文藝片的歷史——片子還未上映,就已經靠預售收入實現票房過億元。實際上,該片首日票房最終定格在令人稱奇的2.6億元。這可是一個讓好萊塢英雄題材大片都會羨慕的數字,也占據了2018年12月31日全部院線單日票房的過半江山。
可此后該片的表現就猶如一場電影都刻畫不出來的夢境——第二日也就是元旦當天,單日票房斷崖式跳水到1116萬元,較首日票房縮水了近96%;而到了元月2日,票房更進一步縮水至184萬元(截至1月4日20:00總票房為2.8億元)。正是因為這樣的戲劇性變化,再加上被舉報首日票房注水,導致華策影視股價開年即出現大跌。
比票房更慘的是影片的口碑。與開映前一片叫好聲不同,看片之后的觀眾表現出了極低的容忍度,在微信、微博上出言吐槽已經是無比寬容,更夸張的是據說有影院經理曬出放映設備遭到損壞的照片,稱幕布被砸出一個凹坑,基本跟“一名成年男性觀眾的拳頭一般大小”。
與此同時,在微博等自媒體或是影視公眾號的評論區,謾罵與力挺的兩種意見又打得不可開交。如果說要從中選擇兩派最有代表性的意見,大致是這類聲音:
A:這類文藝片本身就不是給你們這些抖音用戶看的,還是看《延禧攻略》這樣的“爽片”去吧。
B:掏錢看了電影還能不讓人罵怎么滴?這樣的電影,“裝”就一個字!

《地球最后的夜晚》豆瓣評分

《地球最后的夜晚》貓眼評分
圍繞這部影片既然能產生如此大的爭論,那么到底是有哪一方做錯了嗎?
先來看看以導演為首的制作方。導演畢贛被電影圈視為不到30歲的青年才俊,首部影片《路邊野餐》口碑上佳。在他自己看來,長鏡頭、復雜的場面調度、反情節等都是他所擅長的特色,這部電影就是要用鏡頭的語言,去無限靠近夢境的真實,至于觀眾能看懂幾分,從來就沒有一個標準,正如1000個觀眾眼中有1000個哈姆雷特是一個道理。由此看來,制作方是沒有做錯什么的。
那么觀眾做錯了嗎?好像也沒有。在跨年夜那么特殊的日子,觀眾沒有選擇去時代廣場看水晶球緩緩落下,也沒有在泰晤士河邊看“倫敦眼”絢爛的煙花,甚至都放棄了在暖氣足足的房間里邊吐槽邊收看各大衛視的演唱會,而是跑到影院里想要度過發行方在營銷中所宣傳的“一吻跨年”的浪漫,可是等來的是混亂的時間線和支離破碎的情節,等來的是影院里滿滿的手機屏亮點和不時傳來的打鼾聲,說好的浪漫在哪里?
那么一定是影片的發行方做錯了!真是這樣嗎?宣傳和發行機構會覺得自己比竇娥還要冤屈。投資自然就是為了要賺錢,做出來的產品,難道非要虧本才高興不成。既然是做營銷,當然是希望能讓更多的觀眾進影院里才對,反正錢包是在你們自己手里,又沒有坑蒙拐騙,更不是強買強賣,以后看片前拜托先了解一下基本情況,不要像某些觀眾說的,看完以后才知道原來這不是一部科幻影片。
那么既然三方都沒有錯,問題又出在哪里呢?有人已經看明白了,說“菜是好菜,只是上錯了飯桌”。
縱觀近兩年中國國產電影市場,賣座的不外乎三類影片:一是《戰狼》《紅海行動》這樣的主旋律題材大片;二是以開心麻花團隊為代表制作的喜劇類型影片,如《羞羞的鐵拳》《西虹市首富》等;第三類是今年異軍突起的現實主義題材影片,如《我不是藥神》《無名之輩》。
對于投資方來說,盡管前兩類題材目前依然還是票房保證,但缺陷在于它都不是紀錄老百姓真實的生活,你總不能今年投拍《戰狼》,明年再接著拍《戰虎》《戰獅》《戰象》《戰豹》,或者再虛構什么《東虹縣財神》,真正擁有群眾觀影基礎的是第三類型影片,以講述百姓身邊的故事為主,這無疑將是未來幾年電影市場的主流。
但回到剛才“菜是好菜”那個話題。生活是需要各色菜式來進行調劑的,不是一個類型的好菜就能滿足所有人的品味。比如《舌尖上的中國》里,盡管普羅大眾更喜歡的是水煮魚、麻辣燙、串串香,但像淮揚菜里耗時費力、極考驗刀工的“文思豆腐”,同樣也是生活中一個美好的點綴,你總不能淺嘗一口就開罵,評論說淡而無味,難吃至極吧。
影視行業同樣如此。既需要關注生活點滴的現實主義影片,也需要有《延禧攻略》《戰狼》這樣的爽劇爽片,同樣也需要考驗導演功力與演員表演的文藝類型影片。
回頭再看近年來的文藝片市場,不乏佳作,但像《聶隱娘》《羅曼蒂克消亡史》這樣的好作品票房表現都不盡如人意。
就像有觀眾在說起《地球最后的夜晚》時,認為看著一個涕淚交流的大男人在鏡頭前花一分多鐘時間連皮帶核吃完整個蘋果是“巨無聊巨沒有意義的事”,也有人會討論影片《聶隱娘》中三個看似毫無意義的長鏡頭:一個羊圈中的悄無聲息的幾只羊;一個有著林黛玉筆下“寒塘渡鶴影”一般美麗意境的池塘;女主人公和師父看著山色變幻、云起云落的場景,約一分鐘時間里沒有一句對白——在一部影片總計100余分鐘的時長里,這三個鏡頭就超過兩分鐘,占據全部成片的大約2%。這可是導演侯孝賢引以為自豪的全膠片拍攝,估計出品方的制片人內心一定是崩潰的——很貴啊,侯導,這可是膠片。
但同樣是類似看上去沒有意義的鏡頭,卻可能成就電影史上的經典。這就像一代影后葛麗泰·嘉寶在《瑞典女王》片尾中一動不動的一個面部特寫,如果不是過了很長時間后眨一下眼,恐怕會有觀眾認為是電影已經定格。就這樣一個鏡頭,已經被視為考驗演員演技與刻畫人物功力的樣本。
所以正如侯孝賢所說,他已經年逾70,拍過那么多年的電影,難道還不知道電影制作方想要什么樣的影片,觀眾又想要看什么樣的影片,可是他就想堅守自己的初心,按照自己的意愿拍一部內心想拍的戲。
同樣回到了剛才那樣的困境——導演想拍自己的作品沒有錯;出品方要付出巨額資本,想賺錢或者至少不虧錢也沒有錯;觀眾想看一部好電影,當然更沒有錯。
這樣一個難題,一時半會估計還很難解開。只有兩個建議:對于觀眾來說,錢包還真是自己的,購票前一定三思,尤其不能讓《**筆仙》之類的爛片在電影市場上劣幣驅逐了良幣;對于投資方來說,《地球最后的夜晚》已經檢驗出了當前文藝片的極限市場容量,即真實觀眾群體約幾百萬、票房億元上下,要想投資不至于虧損,一定要算好這個成本賬。
最怕的一個后果是,《地球最后的夜晚》透支了未來幾年市場對文藝片的票房信任,以至于從此以后這就成了一個無人敢于問津的類型片。我們假設一個萬達電影的人士碰到一個阿里影業的人士,見面寒暄說“聽說你最近在投拍一部文藝片”,對方憤怒地回嗆道“你才拍文藝片,你們全公司都拍文藝片”。
要果真這樣,也不是中國電影之福。